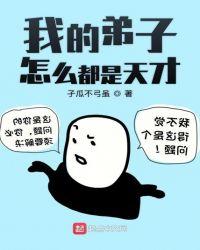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替嫁后我在古代扶贫 > 第170章(第1页)
第170章(第1页)
她动作十分谨慎,生怕一小小心就将伤口弄得更严重,也怕把人弄疼,擦两下就要捧着再吹一吹,似乎这样能减轻一些痛感。感觉到这只大手的手指微不可察地动了下,沈灵语急忙抬起头:“弄疼你了?”“没有。”赵景行看着她笑,“就是有些痒。”沈灵语有些窘迫:“那不吹了。”“嗯。”赵景行收回手,从托盘中拿出药瓶,均匀的将药粉撒上去。沈灵语看着都疼,这人却面无表情,还安慰她说没什么感觉。她一点不信,又想起什么来,这才有空问起:“你是不是故意受伤的?”赵景行撒药的动作顿了下,说:“谁会傻到主动受伤?”“你少诓我。”沈灵语接过他手中药瓶放好,换了棉布递给他,“你那般身手,即便没设防,只要拉着我躲开就是,何需用手去接飞刀,分明就是故意的。”她停了下,鼓起勇气道:“你该不会是心中自觉对清蓉有所亏欠,才”“我没有。”赵景行失笑,“你怎么想到那里去了?”“不然你为什么要去接?”若真是那样,她,她赵景行没想到事态竟这样发展,手上包扎动作了停了,拉着她的手轻叹一声,无奈道:“好吧,我的确是故意去接的。”竟然真是这样!沈灵语心中一急,愤愤地甩开他的手。“但我不是因为清蓉。”赵景行又抓了上来,神情有些尴尬,目光闪烁道:“是老师说,关键时刻,说不定苦肉计能行得通”“苦肉计?”沈灵语无语,“亏你想得出来。”何公怎么连这些也要教吗?反正说都说了,赵景行干脆直白道:“可你还是心疼了,不是吗?”“你!”沈灵语气结,转过身不理他。赵景行唤了两声,也没得到回应,只好悻悻地自己包好手。才低头凑到她颈间,小声喊:“夫人?”沈灵语手中正一件件将首饰继续往盒子里放,赵景行见了忙伸手按住:“不是不走了吗?”“哼。”她手中拿着的,正是之前赵景行送她那支珠钗,她很喜欢,经常戴在头上。钗身是空心的,轻盈剔透,光滑润泽,散发着莹莹光辉。她将珠钗轻轻握住,道:“先收起来,若哪天你变心了,我好方便搬走。”赵景行将下巴枕在她肩上,双手环住她的腰,说:“我有夫人足矣。”沈灵语被他一口一个夫人叫得耳朵发热,哼道:“那清蓉又是为何在你府上?谁知道你还有没有别的夫人…”她越想越不对劲,不禁拿手肘将他推开,“你别碰我,你不守男德,不遵夫道,我才不是你的夫人!”赵景行哭笑不得,揽着她的腰贴紧了些,任她怎么用力也推不开,忙解释道:“我哪里来那么多夫人?自十六岁起我就常年在边郡,那边全是大老粗的男人,回来的时间甚少,连姑娘的手都没牵过,今日还是头一遭,更别提其他……”他说着便意有所指地低笑一声,“你感觉不出来么……”他这话说得沈灵语下意识回味起方才的吻,直感觉被差点咬破的唇又有些肿疼,心跳止不住的又快起来,却还记得先前清蓉说过的话,不由得拿手指着一边的榻说:“那你和清蓉呢?你们不是还坐在那里喝茶对弈,琴瑟和鸣吗!”她越说越气,忍不住更用力地推拒着:“你、你好脏,别碰我!”“我没有…”赵景行皱着眉,无奈地盯着她,“她年幼时也算官家小姐,可惜父亲丢了官,被户部陈侍郎收养,改名换姓,跟着宫人学琴跳舞。本是要送给圣君的,结果阴差阳错地送到我屋子里来了,那时我恰好受了伤,卧在床上连杯子也握不住,她以为我是圣君,便照顾了我一夜。这样一来,我不得已只好将她收进府中。我不知道她跟你胡扯了什么,但我没和她喝茶对弈,也没有琴瑟和鸣。”沈灵语看了他一会儿,嗫嚅道:“真的?”“你若不信,去问月儿。”“他是你的人,说的话才信不得。”赵景行趁机低头在她唇边揩油,说:“你才是我的人。”“你…”沈灵语一时没设防,被亲的脸又红了,羞道:“你好烦…赶紧出去!”赵景行厚着脸皮说:“这是我的房间,我要去哪里?”这话说出来,沈灵语才意识到,马上就要睡觉了,难不成赵景行还不走?她看了看不远处的床,上面还铺着大红喜被,甚至惹眼。赵景行也看出她羞涩神情,眸中噙着坏笑,故意道:“夫人,天色已晚,不如我们歇了罢?”“我、我…”她‘我’了半天,最后支支吾吾道:“我还不困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