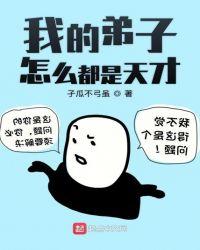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再逢明月 > 第8章日仄是下午的意思(第3页)
第8章日仄是下午的意思(第3页)
起先钟音轻快,是幼鸟在枝头啁啾嬉戏。手腕下移,中间那列甬钟之音闯入此曲,钟音自在悠扬起来,这时是鸟儿长大在林间悠游。她又抬手回到原处,钟音渐缓,变得哀婉,是鸟儿受伤,在雨夜停了呼吸。
他立在殿外等候,不知被景和乐中哪一样迷了心神,竟然感受到久违的松弛。九年来每一日都在梦中撕扯着他的仇与耻被淡忘了一瞬,让他能够看见污沼以外,能够想起自己是人,是一个有血与肉,知喜与忧的人。
“进来罢。”缪妲放下木槌,闭目趺坐在席上休息。
只是一瞬而已,牧黎复而清醒,步入殿中。
“给我擦汗。”缪妲累了,眼睛仍旧闭着,微抬下颌。
为了春祭,她近来日日沐花瓣浴,此刻薄汗冒出,身上亦散着幽幽花香。
牧黎跪在她身侧,拿出未用过的锦帕,轻轻擦拭过她的额,脸,最后是颏。察觉到锦帕离开,她把头又抬高了些,轻哼催促。
几缕碎发缠在粉白脖颈,落入他的眼中,脆弱如厮。稍作迟疑,锦帕覆上她的颈。
察觉出不对,缪妲一把抓住这手,睁开眼睛,对上一脸无措的牧黎。
“是你?”缪妲拍开他的手,他去取信为何回得如此之快?本该是婢女阿鱼在殿外等她。
牧黎双手将锦帕奉给她,“方才少主人只说擦汗,是十三愚钝冒犯,请少主人责罚。”
他的眼神如此诚恳,话里话外还带了委屈。缪妲自己擦了颈间的汗,将锦帕扔在他身上,此人明明是故意一声不吭,她问道:“阿鱼在何处?”
“我不知,少主人可要我去寻她?”
“不必,信给我。”
牧黎从怀中取出信帛交到她手中,见她颊边浮出一抹粉,不知是累的还是气的。
缪妲笑的时候少,生气的时候更少。细数这还是他第一次惹她不悦,她也只是瞪他一眼。
因着刚刚屏退了寺人婢女,殿中尚未燃起烛火,缪妲展开写得密密麻麻的帛书,就着晚日余光一时竟看不清楚上面的字。
她将帛书叠好收入袖中,起身离去。
牧黎自然注意到了,平日里对少主人关怀备至的十三此刻却缄口不言。
*
一阵叩门声将牧黎拉回现实。
“廷尉,你可醒了?上朝要迟了。”田禄在内室外不断叩门。
说来奇怪,廷尉这些年来无一日上朝时睡迟过,有时起得比自己都早。不止早朝,他其实每一日都起得很早,田禄有时也怀疑廷尉到底睡没睡。
今日这般反常,他不由担心起来,扣门扣得更响了。
“滚出去”牧黎掷出杯盏摔在门格田禄的影子上,门外动静立刻消失。
一室静谧重新回来,他闭眼就能看见缪妲的清眸,朱唇,雪颈。咽了咽,只觉又干又渴,身下热物高涨。
他从枕下取出一方旧锦帕,一只长臂搭在软枕之上,半撑半躺。不久,床上人的息变得沙哑,混乱,间或有压抑不住的低哼。
待锦帕洇湿浸透,牧黎起了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