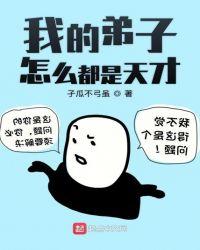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莲歌向晚 > 第 61 章(第1页)
第 61 章(第1页)
托范进转交书笺,书生回来只说办妥了,寒了张脸,径自去针箩里取了绣花针,锦上走线。
“那莲塘大人不必去了,我母后说永世不要见我!”我撇唇道。
书生执目看了我一眼,噙着些冷笑,未感意外。
“铎壬太子呢?”
“我大哥他只问我为何剪发?”
“公主如何回的?”
书生银针飞舞,须臾已绣出朵像模像样的梅花儿来!
“我说因没看上赛马,我发急!”
我瞧着那精细的绣活,发了半天的呆,兀自一笑,那方一记流光慑人,殿中霎时清冷。
“你有气就吐出来,我怕你憋在心里闷!”我讨好道。
“微臣不敢!公主三日内,不妨好好绣个花样出来,若绣不出,范进请辞!”
书生将那针箩摔于我面前,起身而走。
“范……范进……”我朝着那方背影嚷。
“那也得绣!待公主想明白了,可随时召见微臣!”书生抛下话儿,头亦未回地出了大殿。
莲歌,你还是公主么?
还不如回乡卖莲藕自在呢!
我叹息着,瞧着笸箩内那明金彩线发憷。
别说是花儿,本殿连个草也绣不出呢?
将那针箩丢在一旁,我跑去了流月处。
“臭丫头,为那不值得的男人,竟把自己的头发也搭进去了!”
流月恨声搡了我几下,亏她没姜尚的力气,我揉了揉肩膀,觉得她这双眼果真没白长。
“流月,你只猜对了一半,并非如你所想,实为迫不得已!”我无奈道。
“甭与我说这迫不得已的话,我已然是死了一般,你倒有点出息,活出个人样儿来!”她瞧着我那头发,当即气的掉了泪。
“流月!你打板子都未哭,何必为这头发伤心?”我愁云遍布道。
“不善待自己的女子,我流月根本就不愿见,让人生不出一点盼头来!”她挑了挑眉,泪水晶莹的美人韵致,惹人深顾。
“看来又是你这执拗害人!说来我以为你在冼宫人处倒是好的,那后宫嫔妃三五日也见不到圣上的面,若遇了冷,就是月月年年,忘了个干净!那秀女中有几个才见过圣上,可也不过是那一日的夫妻,赐如意、绣宫,皆是痴人说梦,听说有一位已大半载未见圣上了,哭的形销骨立的!”我好心劝道。
“他既打了我,我流月便不能放了他!”莹黑的美眸一冷,美人吃了秤砣铁了心。
“因那顿杖责,你恨圣上?”观其斩钉截铁的模样,我不由地一问。
“不是恨,是觉如何不问青红皂白就降罪于人,有失公允,实则我与王昭容相处甚好,倒是那沈婆子才该被拖出去,乱杖痛打!想我流月,自宫外,哪个男人见了不疼?如今在这宫里竟被打了个血肉模糊,我死不瞑目!”说着,她的目光又坚然起来。
“凭什么世间男人就该都疼着你?我且嘱你一句,这圣上是天下最讲理的人,也是最不讲理的人!若遇到他讲理时,会觉得他是明君,若遇到他不讲理时,会觉得他是昏君,躲远了才是正理!”
对于她的自恃甚高,我时常无计可施。
大哥说流月不是寻常女子,我对比自己,以为的确如此,对照他人,更觉尤甚。
“嘘——,这话如何说得?头发才失了,再失了脑袋!”流月闻言,瞪我一眼,小心向外瞧了瞧,掩好了门扇。